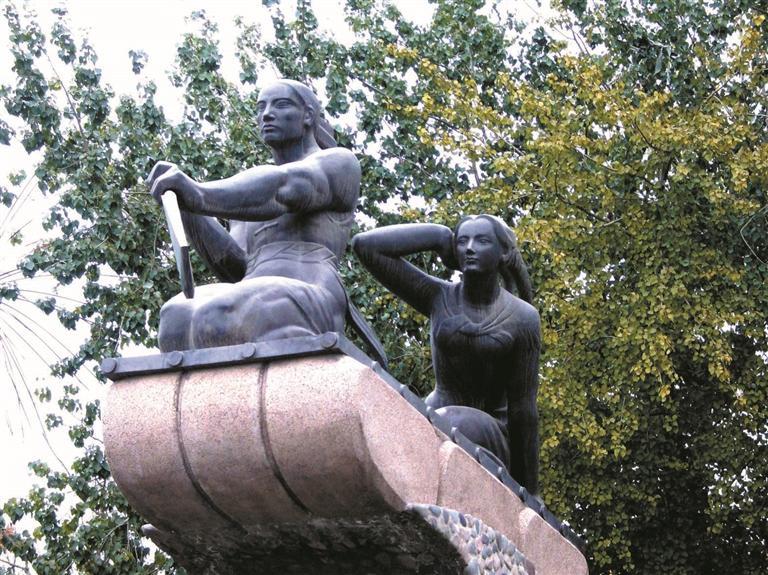梁曉聲:我在北京四十年

屈指算來,我從復(fù)旦大學(xué)畢業(yè)后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已經(jīng)44年了。
我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有半年左右的時(shí)間沒宿舍可住,臨時(shí)住北影招待所的一張床位。半年后分到了一間單人宿舍,11平米。那是筒子樓,家家戶戶在走廊做飯,每日三次,走廊里定時(shí)響起鍋碗瓢盆交響曲,人們邊做飯邊聊天,十分熱鬧,關(guān)系也都非常好,很少發(fā)生過爭(zhēng)吵現(xiàn)象。
我在11平方米的家里有了兒子,做了父親。三四年后,廠里分房,我搬了一次家——從走廊這頭搬到了走廊那頭,家大了,14平方米了。我顧不上粉刷,將老父親從哈爾濱請(qǐng)來,幫我接送入托的兒子。老父親當(dāng)天鄭重地對(duì)我說:“兒子,你一參加工作就分到了住房,而且還是木板地,有福啊,你知足吧。”我確實(shí)很知足。
當(dāng)年,許多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是分不到住房的,某些單位連集體宿舍也無法提供。而我們那筒子樓里,不但住著入職一二十年的老職工全家,還住著幾位夫妻兩地分居的科長(zhǎng)、處長(zhǎng)——他們已經(jīng)與家眷分居多年了,家眷很難調(diào)入北京。
我的老父親不可能與我們夫妻共同住在14平方米的家里,老母親也不可能與老父親同時(shí)來京,那就更沒法住了。我為老父親買了一張折疊床,他每晚就睡在我的辦公室。
老父親離京返哈,老母親才接踵而來。
幾天后,老母親問我:“兒子,你不是分到北京了嗎?”
我說:“是啊,咱家不就在北京電影制片廠院內(nèi)嗎?”
老母親說:“可北影大門外哪兒像城市啊?這地方不是叫什么太平莊嗎?敢情你是名義上分到了北京,單位實(shí)際上是處在一個(gè)莊的地面啊!兒子,那你的城市戶口還保留著嗎?”老母親一臉憂慮。我費(fèi)了好多口舌才打消了她的憂慮。
當(dāng)年北影大門外那條路叫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16路公交的一站正對(duì)北影大門。那條路僅中間部分是柏油鋪成的,而且處處龜裂,有的地方還塌陷了。柏油路面的兩旁是沙土路。也不僅那條路如此,縱橫于那一帶的路全那樣。
北影對(duì)面是中國教育出版社,它的院門和主樓當(dāng)年算是“氣派”的,現(xiàn)在看自然尋常得不能再尋常了。它的右邊是部隊(duì)家屬院,再右邊是北太平莊商店,那一地帶最大的商店,只一層,內(nèi)外都很老舊,面積五六百平方米。秋末也在店外賣大白菜,小丘般的菜堆常碼在人行道上。往往,人們起早貪黑地排長(zhǎng)隊(duì),唯恐買不到。
北太平莊商店是馬路那一側(cè)的終端。中國教育出版社的左邊除了幾處平房,再就沒什么建筑物了。平房更左邊,是一小片野草叢生之地,狗尾草居多。而北京電影制片廠這一側(cè),右邊是一片菜地,屬于所謂“城中村”。左邊依次是部隊(duì)干休所、新聞電影制片廠。新影左邊,似乎曾有一處小旅館,便也到頭了。
那時(shí)我年輕,單身時(shí)偶爾晨跑——從北影向右,跑過菜地轉(zhuǎn)彎,一直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那邊跑,再轉(zhuǎn)彎經(jīng)過北醫(yī)三院,跑跑走走回到北影。所經(jīng)雖然都是北京有名的單位,但周邊未免荒涼。于是也會(huì)像我老母親那樣想——我真的算是北京人嗎?也許說是某“莊”之人更恰當(dāng)吧?
幾年后,新影左邊的小旅館拆了,建成了10層的遠(yuǎn)望樓。它在當(dāng)年使不少北太平莊地區(qū)的居民為之喜悅,都說從此北太平莊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了。
10年后,北影門前修起了高架橋和過街天橋——那條路成了三環(huán)之一段,而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也在曾經(jīng)的菜地上開始修建了。
三環(huán)的出現(xiàn)似乎是一道界限的劃分,那邊算市區(qū),這邊叫“環(huán)外”。“環(huán)外”有接近市區(qū)的意思,也有終歸不屬于市區(qū)的意思。三環(huán)曾使北影、新影的職工及家屬一度失落,因?yàn)榉置鞅粍澋搅耸袇^(qū)以外。
40年彈指一揮間。如今的北京,五環(huán)內(nèi)外已經(jīng)處處高樓林立,新區(qū)多見,繁華多了。居住在三環(huán)邊上的人家,等于居住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了。
1988年底,我從北京電影制片廠調(diào)到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那時(shí)北京電影學(xué)院從郊區(qū)遷入市內(nèi)了,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大樓也蓋起來了。
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北京電影學(xué)院、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3個(gè)單位,同處于橫豎兩條主要馬路交叉的直角地帶。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在三環(huán)邊上,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在健安西路邊上。
健安西路是一條極短的一頭“堵死”的小街。也不是完全堵死了,只不過機(jī)動(dòng)車是通行不過去的,但步行或騎自行車的人,可穿穿繞繞地到達(dá)前邊的橫街。這條小街的一側(cè)是一家便民飯店、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宿舍樓、北京電影制片廠宿舍區(qū)后門、前進(jìn)小學(xué)、部隊(duì)干休所后門,另一側(cè)是元大都土城墻遺址,土城墻顧名思義是土堆成的。
當(dāng)年那條小街極幽靜,“遺址”卻只能用幽靜來形容。其上有片老樹林,此外野蒿遍布。其間有條臭水溝,名字卻起得很好,叫“小月河”。天黑以后的“遺址”,即使是膽大的人,也寧可繞遠(yuǎn)而決不圖近便從遺址中穿過。連公安部門都提醒,那是很不安全的。
不知從哪天開始,小街上出現(xiàn)了攤車,不久又出現(xiàn)了地?cái)偂>用裼X得方便,東西也便宜,以樂見的態(tài)度接受之。于是賣主們將那條小街當(dāng)成了擺攤的固定地點(diǎn)。
一個(gè)月后,不得了啦,從早上6點(diǎn)到9點(diǎn)多,有時(shí)到10點(diǎn),小街幾乎水泄不通了。就是兩手空空的,也得側(cè)身才能通過。而那個(gè)鐘點(diǎn),正是家長(zhǎng)們送孩子上學(xué)的時(shí)間,也是“干休所”老干部們乘車出行之際。小街上的居民本沒那么多,因?yàn)橹苓叺木用褚瞾砹耍圆艜?huì)形成人擠人的局面。賣什么的都有,現(xiàn)場(chǎng)炸油條,煮餛飩,蒸包子,烤肉串,煎鍋貼,更使整條小街煙氣繚繞,雜味彌漫。那時(shí),窗子臨街的人家是不能開窗的。
小街終于安靜下來以后,遍地垃圾。雨后,流淌著的水是黑的,浮著油花。
那條小街重鋪過一次,煥然一新的面貌僅保持了一兩個(gè)月。
2000年,我家在牡丹園北里買了房子,那條叫小關(guān)西街的小街,起初也很幽靜。小區(qū)多了,居民多了以后,同樣地,逐漸變成了一條臟街。路面重鋪過一次,也很快就恢復(fù)其臟了。街道干部出面協(xié)同各方著力治理過一次,還成為新聞上了電視,街道干部還在電視中引用了我呼吁整頓的話。
只不過治理行動(dòng)一過,臟亂差的程度與之前相比,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幾年前,全市范圍的大治理開始了。由于預(yù)先宣傳得充分,道理講得明白,而且不再是單獨(dú)局部的行動(dòng),而是全市統(tǒng)一的行動(dòng),可以說所到之處,進(jìn)展順利。
健安西路那條小街終于又幽靜了,干凈了。土城公園更美了,成為了北京很有特色的一處街區(qū)公園。小關(guān)西街也干凈了,還出現(xiàn)了美化街道的公益景觀。
并且,治理過程沒發(fā)生矛盾,一切順順當(dāng)當(dāng)?shù)鼐桶言撟龅氖伦龀闪恕J聦?shí)證明,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支持的,并且因?yàn)榭吹搅撕玫慕Y(jié)果而點(diǎn)贊。
如今,北京治理“臟亂差”現(xiàn)象的工作,成效喜人,有目共睹。正在進(jìn)行的,是對(duì)老舊小區(qū)的深度改造,而這也是提高民生水平,深得人心之事。
我的外省朋友們,曾來過北京的,又來后都說:“北京比以前干凈了,比以前美了。”他們的表揚(yáng)指的是北京的“肌理”,即像健安西路和小關(guān)西街那樣的小街小胡同。
第一次來北京的朋友們則說:“放眼望去,無違章搭建,整潔美觀,不愧是首都。”
一個(gè)相關(guān)的問題是——若擺攤確系某家某戶的生計(jì),后續(xù)扶貧工作是否跟進(jìn)了呢?
據(jù)我所知,各級(jí)政府扶貧工作也在扎實(shí)推進(jìn)。
一日我走在小關(guān)西街,見一家小菜店將菜筐擺在門外兩旁,那就占了人行道了。街道管理員當(dāng)面批評(píng)店主,命其將菜筐搬入店中。店主連聲道歉,表示接受批評(píng)。
城市管理者應(yīng)當(dāng)明白,民之可與不可,在于如何養(yǎng)成良好習(xí)慣,培養(yǎng)公德意識(shí),絕非一朝一夕便可立竿見影,必待長(zhǎng)久之功。
盡管,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但首先是北京人民的北京——故北京人民和各級(jí)政府為創(chuàng)建“美好首都”所做的種種努力,定會(huì)獲得全國人民的點(diǎn)贊。
那么,讓我也在此為日漸美好的北京由衷點(diǎn)贊!(作者:梁曉聲 本文為北京文聯(lián)慶祝建黨百年特約原創(chuàng)文學(xué)作品)
相關(guān)新聞
- 2021-06-07朱德庸:幽默是一種慈悲
- 2021-06-07@所有人,您有一份來自王蒙老師的“青春書單”,請(qǐng)查收
- 2021-06-07特寫:“勝利的時(shí)候,請(qǐng)你們不要忘記我們!”
- 2021-06-07《永樂大典》的編纂、流失與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