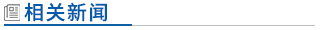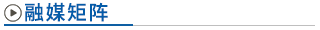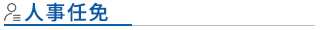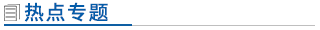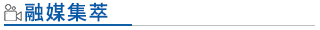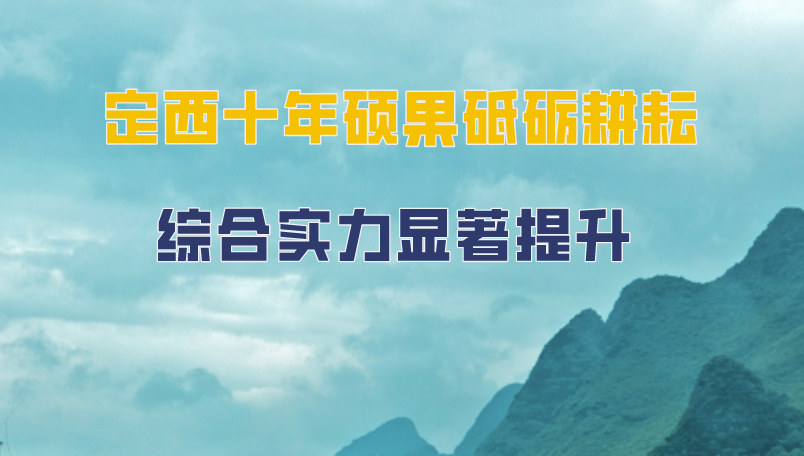2009年8月,我陪同北京進藏調(diào)研的領(lǐng)導(dǎo)到林芝出差。從拉薩出發(fā)時,還是晴空萬里,風(fēng)和日麗,臨近拉薩和林芝的界山米拉山時,卻見前方烏云密布,風(fēng)雪欲來。說話間,窗外就飄起零星小雪,隨著海拔的升高,雪也越來越大,到了離山口大約一公里的地方,已經(jīng)是鵝毛大雪,道路兩側(cè)的山上白茫茫一片,甚是壯觀。
走了一會兒,只見幾十頭牦牛一邊悠然自得地在雪地里散步,一邊雜亂無章地拱著雪下的青草。離牛群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黑帳篷,裊裊炊煙從帳篷頂上面的煙囪里飄出來。
來到帳篷前,陪同調(diào)研的藏族干部洛朗先走進帳篷和主人打招呼,不一會兒,放牧的大哥和洛朗一起走出來,伸出雙手,熱情地邀請我們到帳篷里做客。
因為牦牛毛編出的黑帳篷嚴密厚實,熱松冷緊,炎炎夏日里,陽光下的牛毛會變得松軟,習(xí)習(xí)微風(fēng)透過牛毛縫隙,給人們帶來絲絲涼爽;到了雨雪天,受潮的牛毛會立刻緊縮,變得如同鋼板一樣堅硬,讓雨水無法滲入帳篷內(nèi)。所以走進黑帳篷,一股熱流撲面而來。只見帳篷中央有個泥土砌成的爐灶,燃燒著牛糞的爐火,讓走進帳篷的人感到無限溫暖。帳篷的一邊鋪有牛皮、羊皮、坐墊等,洛朗說這叫“陽帳”,是男主人活動的區(qū)域,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另一邊擺放著燒茶煮飯的廚具、糧食等,自然是“陰帳”,是女主人活動的區(qū)域。
放牧的大哥熱情地向領(lǐng)導(dǎo)獻上潔白的哈達,然后把領(lǐng)導(dǎo)引到上座,他自己則在下座。與此同時,女主人一邊往爐灶里添著干牛糞,一邊開始制作酥油茶。只見她用茶刀從一塊磚茶上切下一大塊,放進一口銅鍋中熬制了10多分鐘,然后把茶汁倒到一個上面鋪有過濾網(wǎng)的鍋中,拿走過濾網(wǎng)后,往過濾后的清茶里放一大塊酥油和少許食鹽,倒入一個木制的茶筒里,用一根頂端裝有圓形木柄的木棍上下抽提起來。領(lǐng)導(dǎo)很是好奇,在征得主人同意后,接過木棍,像模像樣地學(xué)打酥油茶。經(jīng)過上百次的抽打,茶、油和食鹽充分融合,女主人把它們倒進鍋里加熱,便成了香味濃郁的酥油茶。
在女主人制作酥油茶的同時,洛朗給我們介紹酥油茶的前世今生。他說,在雪域高原,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說法。這是因為在藏族人民的飲食結(jié)構(gòu)中,乳肉類占很大比重,而蔬菜、水果較少,因此藏族同胞以茶佐食,餐餐必不可少。洛朗告訴我們,其實,制作酥油茶最關(guān)鍵的還是酥油的提取。一般要先把新擠出的牛奶或羊奶加熱,趁熱倒入酥油桶(一種專用的大木桶)中用力上下抽打,經(jīng)過上百次的抽打以后油水分離,這時在它的上層會有一層黃色的油脂出現(xiàn),把它取出來放到皮口袋中,經(jīng)過冷卻以后,就能得到塊狀的酥油。夏季的米拉山草肥水美,是產(chǎn)奶旺季,此時提煉的牦牛酥油品質(zhì)最佳,色澤鮮黃,味道香甜,口感極佳。
喝酥油茶所用的茶具也非常講究,所用的壺大多為金屬制品,比如銀壺、銅壺、鋁壺、瓷鐵彩花壺等,壺嘴、壺把造型別致,壺的頸腹部大多繪有彩色民族圖案;所使用的茶碗則大多為木制或是陶瓷制品,上面有銀或是銅鑲嵌。
說話間,女主人已把酥油茶加熱好。在這個帳外雪花紛飛、帳內(nèi)熱氣騰騰的黑帳篷里,藏茶在沸水中翻騰,炒熟的青稞散發(fā)著淡淡的清香,燃燒的牛糞散發(fā)出干草香,和著酥油茶濃郁的氣息沁人心脾。女主人走到陰帳那邊拿出一摞鑲著銅邊的木碗,一一擺到我們面前,給木碗里倒?jié)M酥油茶。女主人一邊倒茶,一邊不停地輕輕搖晃茶壺,以使酥油茶變得更加均勻。
喝過幾口后,我們跟著洛朗把木碗放回桌子上,女主人再把木碗添滿。洛朗說,酥油茶是藏族群眾每日必備的飲品,居家自不必說,辦公的時候也經(jīng)常會派人出去打一壺酥油茶回來大家分享。但能在冰天雪地里的黑帳篷中喝新鮮牛奶制作的酥油茶,真的十分難得。
介紹完喝酥油茶的種種好處,洛朗提醒我們,到藏族朋友家做客,酥油茶不能喝一碗就走,一般以喝三碗為吉利,正如拉薩諺語所說:“一碗成仇人,三碗兄弟情。”他勸我們盡量多喝一些,這樣一會兒上米拉山口的時候頭就不會痛。
制作酥油茶要實現(xiàn)茶、油、鹽的水乳交融,而我們在米拉山的黑帳篷中,在歡歌笑語中與牧民大哥和女主人一起制作酥油茶,一起品嘗酥油茶,又何嘗不是藏漢同胞水乳交融的過程!
(作者系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jīng)理)
- 2022-10-08讀書從來都是寂寞的事
- 2022-10-08美器
- 2022-10-08今日寒露丨人間醉美是秋天
- 2022-09-23今日秋分丨恰是人間好時節(jié)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國
學(xué)習(xí)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