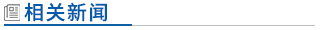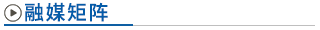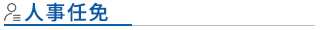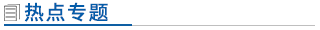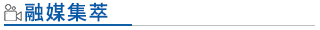作者:張鵬禹(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
胡竹峰的散文集《惜字亭下》(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看書名,即有古意。古人有敬惜字紙的傳統(tǒng),使用過的紙張不可隨意丟棄,拿到惜字亭,付之火中,那些凝結(jié)了先人智慧的文字,不論隸書、行書、草書,還是工整的蠅頭小楷、孩童習(xí)書的歪扭字跡,都在煙塵繚繞中,一起回到倉頡的懷抱。其中自有一種敬畏,而做文章最需敬畏。站在惜字亭下,胡竹峰回望遙遠的過去,反觀當下的生活,將山川草木、鄉(xiāng)野閑趣、水墨丹青等落諸筆端,其中有對自然萬物、生死命運、傳統(tǒng)習(xí)俗的敬畏,更有對中國文章的敬畏。
《惜字亭下》分為五輯。寫古物,老畫、舊書、古環(huán)、銅印等是打開時光隧道的鑰匙,作者以此為引子,在與古人的對話中譴興抒懷;寫鄉(xiāng)野,花草風(fēng)露、四時榮枯,盡顯作家的格物功夫,而放牛、訪竹、斗羊、對月等人與自然的互動,則溢滿作家的生命體驗;寫飲食,品百味、搜野菜、嗅茶香,百般滋味如人生;寫行旅,山川行勝,大江大河,錦繡風(fēng)光,看風(fēng)景,看到的亦是人生;寫戲曲,基于歷史背景與徽州民俗訴說觀戲體驗,勾畫出活潑的民間生活世界。
《惜字亭下》意脈貫通,一氣呵成。且看《云深》一文,作者從宋元古畫里的云起首,云白印紅,說舊時朱砂顏色好,紅得有體溫。畫里舊時煙云未散,四時云景不同,而古人素有“集云”傳統(tǒng)。作者亦曾訪云,深秋到山里,體會過《尋隱者不遇》的況味,但名為觀云,實則觀的是心情,觀的是人生況味:“人生無非兩種境地,如江河洋洋歸于大海,海上生明月,靜而闊,浩渺一片。又或者緣溪而行,上到深林白云間,山色空蒙中。”
我尤愛書中的短章,多是不足千字的小品。短文自有短文的妙處。短文章有古意,古人惜墨如金,太史公春秋筆法,一字便有微言大義。這本集子里的文章長短相宜,相映成趣,穿插排布,令人讀之清爽。譬如《玲瓏》用小文章寫小文章的好:“小文章意思在小巧玲瓏,有庭院氛圍;洋洋灑灑的宏闊長文章,沒有這種風(fēng)味。”作者繼而發(fā)出感慨,文章玲瓏就好。做文章貴在有味。乏味的東西,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從一些篇什看,作者好似一個只讀古人書的迂夫子,其實書中的生活情趣與煙火升騰,也在表明這是一部世間書。《地氣》在春秋代序中,走入田野和山林,不乏童心。《懸天》講藏地異域風(fēng)情激活作者神經(jīng),與友人的宴飲之樂釋放了沉重的肉身。文心本來就需要生活滋養(yǎng),胡竹峰不過是多了些古人之心罷了。換個角度想,散文不唯是真情實感的藝術(shù),更是虛實相生的藝術(shù)。胡竹峰古書讀了幾十年,其中的百代風(fēng)華滲入生活,構(gòu)思行文中也便有如在目前之感,寫出來的東西就不唯“實感”而偏向“虛感”了。“虛感”不是虛假,而是“真情”的另一種產(chǎn)物。有時候,情愈真,登山情滿于山,觀海意溢于海,所見“眼中之竹”便難再“實”了。因此,若拘泥于作者在某時某刻是否真想到古人哪件事,那便是不解風(fēng)情。胡竹峰的言志抒懷,也是在建構(gòu)一個探尋中國文脈的寫作者形象,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一種尋找——尋找一種恰切的方式,將文脈延續(xù)中撿拾出的瓔珞形諸文字。在這種尋找中,胡竹峰有鮮明的文體自覺。中國精神、文言傳統(tǒng)、雅正白話是他孜孜以求的“好文章”。這種“好文章”還要學(xué)古而不泥古,生機勃勃,如他所說:“生機是文章第一要義。”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8日 12版)
- 2022-10-25居于城市的“寓言大師”
- 2022-10-25從行走與閱讀中領(lǐng)略文學(xué)的風(fēng)景
- 2022-10-25于一行行文字里聆聽文學(xué)的足音
- 2022-10-25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如何創(chuàng)新發(fā)展?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國
學(xué)習(xí)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