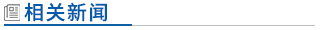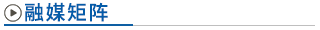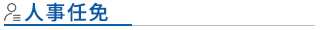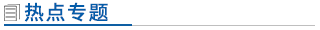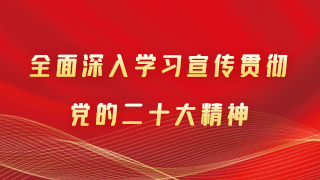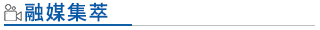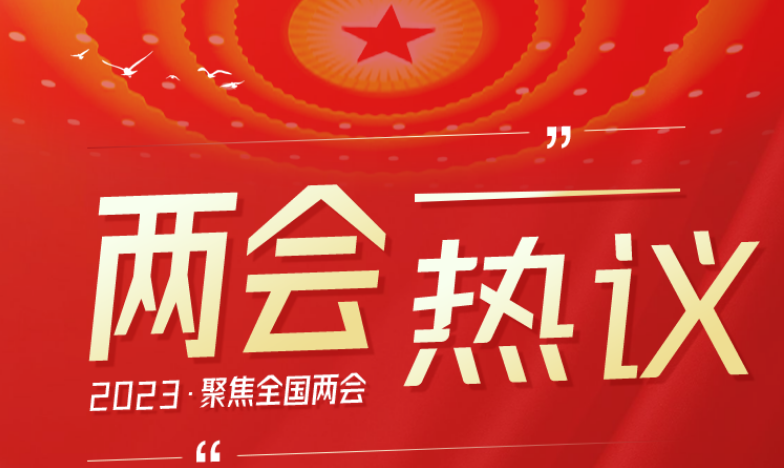編者按
《北方廚房:一個家庭的烹飪史》是作家蔣韻的非虛構新作。本書以奶奶、母親、“我”三代女性的主廚食譜為經,以開封、太原、香港等城市空間的輾轉為緯,串起了一個北方的行醫世家——孔氏家族長達七十年的風風雨雨。本文作者認為,這部作品不僅限于一個家族的烹飪小史,蔣韻從打撈“吃什么”出發,認知和體恤自己的生養之地,沿途親歷的人和事都成為自我求證的歷史證言。
每次面對蔣韻的新作,如同面對一個即將打開包裝的禮物抱有期待。你會發現,她的作品有很強的代入感,因為她擅長營造一種氛圍,讓你不由自主進入她的寫作情境當中。
“從哪說起”,是一個作家每次提筆都會面臨的難題。某種意義上,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在《北方廚房:一個家庭的烹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版)中,蔣韻開篇設置了一個場景,就像一個蒙太奇鏡頭,將時空拉回到200年前的法蘭西,引出美食家薩瓦蘭的一句話:“告訴我你吃什么樣的食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這個開場白,對蔣韻而言非同尋常,這是一個激活靈感的寫作“契機”,如一束光,照亮悄然沉寂的過往,領她與過去的自己相見,與家族歷史相見,與生命中的故人相見。
這是一次美食鋪路搭橋的靈魂邂逅,于是,想象薩瓦蘭還健在,“我寫,他看。”“親愛的薩瓦蘭先生,請您煮一壺香濃的咖啡,我開始了。”這個頗有儀式感的文學表達,令人陡生好奇,那是怎樣的一場旅行?除了寫一個家族的菜譜小史,蔣韻還想表達什么?這個別出心裁的開篇,虛擬了一個穿越式的對話情境,由“我”(蔣韻)如實寫出自己吃過的東西,請“他”(薩瓦蘭)告訴“我是什么樣的人?”這里植入一個潛在的命題:一場循著味蕾從舌尖出發的自我求證之旅。走出虛構,返回“民以食為天”的“食”,到一日三餐的舌尖上尋根。
串起生命中遇見的那些有趣靈魂
關于寫吃,作家們各有各的文學經驗。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寫到,自己曾經屢屢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味道“極其鮮美可口”,“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溫情的回味背后,魯迅不忘“戳穿”那是故鄉蠱惑他的“誘餌”。蕭紅的《商市街》則把饑餓寫到力透紙背呼之欲出。在極度饑餓之下生發的幻想竟然是列巴圈可不可以偷吃?桌子能不能吃?汪曾祺關于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時期的云南美食,家鄉高郵的小吃,文人的雅士趣味和“風物志”趣味兼而有之。
上述文字都是散文,自有“非虛構”色彩。虛構類的小說,我印象最深的,是20世紀80年代,陸文夫有一篇直接以《美食家》命名的小說,讓一個“吃貨”堂而皇之回歸舌尖走進文學殿堂,也是當時文學從宏大政治敘事回歸日常生活的象征之一。此后“美食家”幾乎成為一個亦莊亦諧的指稱。
在蔣韻這里,吃是一件有愛有趣的事情。尋常人家的廚房廚藝在蔣韻筆下活色生香、善解人意。不但如此,經由蔣韻勾勒的食物鏈也是一條有“閱歷”有溫情的歷史珠鏈,串起在她生命中遇見的那些有趣的靈魂。重拾每一種吃的感受(也是活著的感受),體味每一個令人縈懷的廚房細節,于蔣韻而言,是握住記憶的根脈,為自己找到不絕的生命之源。豬油渣的神奇妙用畫出一日三餐的精魂,產生靈魂出竅的藝術效果,桂花年糕“好吃到我簡直要飛翔起來”讓我們領略美食刺激之下的巔峰體驗,蔣韻筆下的食譜“都是讓我靈魂歡唱的美味”。
一瓢飲一簞食不無故事,家族內外人情世故都有來歷。她從打撈“吃什么”出發,認知和體恤自己的生養之地,沿途親歷的人和事都成為自我求證的歷史證言——除了真實的“吃相”,也直達人的靈魂真相。
蔣韻所呈現的不僅僅是食材,沒有她個人色彩的記憶附著其上,也許不過是平淡無奇的一頓飯而已。記憶的“碎片”經過美食的“組織”“編排”“敘述”,往事與故人重又聚集起來,像一串閃光的珠鏈,映照出自我與歷史的面容,從而有了新的味道。蔣韻讓我們記住美味的同時記住了那些有著生活智慧、靈魂散發香氣的人物——奶奶、母親、鄰居、朋友、同道、閨蜜乃至保姆阿姨。流動的廚房餐桌,因圍攏它的人而升華了美的味道。從食物的營養美味汲取其中更深邃的精神滋養,輻射到聚攏在餐桌周圍的家人、鄰居、朋友身上,萃取真摯的性靈溫暖,蔣韻無疑寫出一種人生體驗或者說藝術經驗。經由“滋味的巔峰”描繪出美食的“善”,與此同時,精神的“善”也達成一致,彼此輝映。
一位作家的尋根之旅
這部非虛構作品的意義在我看來絕不僅僅限于一個家族的烹飪小史或簡史。那些來自廚房的鮮活經驗,也成為解答個人成長奧秘的鑰匙、滋養美好人性的溫床。設若不是蔣韻曬出這份“主食”,我們或許并不能充分了解她的體質、精神和情緒。蔣韻是一個出生于1950年代北方城市的女孩,從曾經的古都故鄉開封走出,身后是以奶奶為首的孔氏家族龐大漸趨消瘦的背影,來到內陸省城異鄉太原,生活在知識分子父母身邊,經歷了共和國三年困難,“文革”十年的動蕩,恢復高考的大學校園,80年代的文學理想與探索,90年代的寫作成熟,乃至新世紀的筆耕不輟,她一腔至誠向我們展示一個作家的“胃口”是怎樣養成的。
家人愛的滋養,時代社會當中美好人性的汲取,這是一種袒示也是一份感恩。如今年過花甲,蔣韻如同站在秋天的沃野,我的耳畔響起《壟上行》的旋律,眼前浮現米勒《拾穗者》的畫面,敞亮的靈魂有了明燈和力量,經由這樣的書寫,蔣韻完成了那個自我求證的隱形命題,回答了向薩瓦蘭發出的穿越之問。
正如學者李小江所言:“就像莊稼的生長需要充足的養分,一個人的人生——無論其身份地位民族種族——不僅需要閱歷和遠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氣與安然。”此番自我尋根與確認,讓蔣韻的文學生命平添一份豐沛健碩,據她自己講,近幾年的寫作速度比年輕時候還要快。這樣的創作狀態對一個作家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幸運。經由自我尋找自我認同,走向對時代的記錄觀照,結語部分對那個設問給出的答案已經不言而喻:關于食草動物食肉動物的思考,延及當下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抵達廣大的人類關懷。從這個意義上,把《北方廚房》當作一部食物啟示錄來讀,也未嘗不可。
(作者郭劍卿,為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教授)
- 2023-03-15繪一幅壯闊的中國文學地圖——《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寫作緣起
- 2023-03-15日常敘事與宏大敘事的詩學統一——讀王躍文長篇小說《家山》
- 2023-03-15探尋重寫文學史的路徑——讀梅杰的《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
- 2023-03-15《詩經》:溫柔敦厚 以文化人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