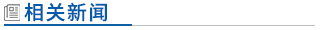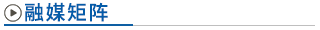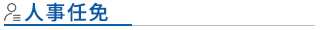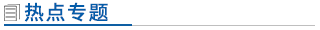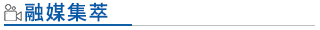阿信
丘成桐,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27歲證明了困擾數學界22年之久的卡拉比猜想,33歲成為第一位獲得數學界最高獎“菲爾茲獎”的華人數學家。
1979年,丘成桐應華羅庚邀請回國訪問,此后他便開始為中國的數學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中國微分幾何方面的人才。2021年,清華大學“求真書院”在丘成桐的推動下成立,致力于在中國本土培養數學領域發展的領軍人才。
《我的教育觀》這本著作融合丘成桐個人成長故事與教育哲學思考,既是他四十余年教育實踐的總結,也凝聚了他數十年治學、育人經驗,為讀者揭示了為學、育人、成才之間的深層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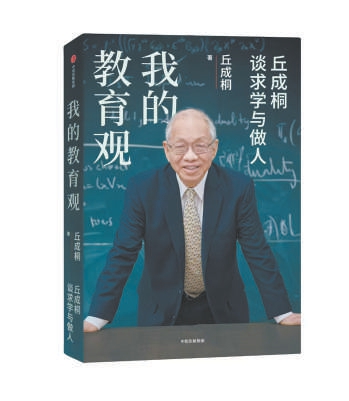
《我的教育觀》 丘成桐 著 中信出版集團
幼年時古典文學熏陶影響深遠
回望自己的求學之路,丘成桐認為父親的教導對他影響頗深。丘成桐的父親丘鎮英是一位飽學之士,即便在生活顛沛流離的困境中,依然矢志不渝地堅守學術理想,并以滿腔熱忱投身教育事業,成為丘成桐一生的榜樣。
在父親的引導下,丘成桐自幼便開始廣泛涉獵知識與書籍。其中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深深影響了我做學問的氣質和修養”。
后來,丘鎮英教孩子們念有關做人與讀書的文章,由淺入深,開始時念《禮記·檀弓下》中的《嗟來之食》,又念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等到了中學,丘成桐開始研讀歷史和哲學相關的書籍,對《史記》尤其著迷,不僅是因為其文字優美、音調鏗鏘,而且它敘事求真、史觀獨特。
雖然年少時的丘成桐還未改鄉村孩子的野性,中學一年級時數次得到了“多言多動”的評語,并且最初接觸這些艱深晦澀的文章,丘成桐總是不解其意。但日夜埋首于典籍的世界,文字里的智慧逐漸在他心中生根發芽。
彼時的丘鎮英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書院,因此還有不少學生到家中和丘鎮英交流,交談的內容包含西方哲學與儒、道、佛等中國思想的融合。
雖然尚不能理解這些哲學思辨,但是丘成桐逐漸習慣了比較抽象的學術討論,讓他一經接觸平面幾何便陷入了對數學狂熱的喜愛。“利用簡單的公理,卻能推導出美妙的定理,這實在令人神往。”
這些似懂非懂的哲學命題在他的心中播下了做學問的種子,古希臘學者對真理和美無條件的追求,也成了丘成桐一生為學的座右銘。
整體性思維訓練至關重要
童年教育對個體成長產生著深遠影響,啟蒙教育作為心智成長的基石,不僅具有不可替代性,更在潛移默化間為未來的學術或職業發展奠定基礎。
丘成桐認為,小學生的功課不宜負擔太重,對孩子們來說,學到多少知識并不是最重要的,興趣的培養才是決定其終身事業的關鍵。
小學時的丘成桐成績并不優異,最終的升學會考雖未名落孫山,卻也因成績欠佳而無緣公立中學,但對學習的興趣成為他一生中永不枯竭的動力。
相比之下,丘成桐認為中國式的教育往往注重知識的灌輸,而忽略了孩子們興趣的培養,很多家長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子補習,甚至開始準備奧數。孩子的心理負擔很重,慢慢視學習為畏途,有的人終其一生都沒有領略到做學問的興趣。
另外,整體性思維的訓練對一流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以數學教育為例,丘成桐認為首先是要讓學生弄清楚學習數學的真正目的在哪里。
學習數學絕對不是為了學習集合或諸如此類的一大堆符號,而是要知道在推導思想方面,數學的方法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去培養的,借此訓練學生主動思考。
初中二年級學習平面幾何時,丘成桐第一次接觸到簡潔優雅的幾何定理,這使他贊嘆幾何的美麗,也是他感受數學與世界關聯的開始。
直到大學時期,丘成桐開始學習高等微積分,在讀到用戴德金分割(Dedekind cut)構造實數的方法后茅塞頓開:連最基本的實數系統都可以嚴格地建立起來,這著實令人興奮萬分。
人們希望用簡潔的數學語言將這些自然現象的本質表現出來,這便是數學之于思維和世界的關系。
除了證明卡拉比猜想,1977年,丘成桐與學生孫理察用幾何分析法解決了廣義相對論中著名的正質量猜想。霍金是丘成桐的朋友,他是物理學界第一個懂得這個證明的人。1978年,他們初次見面,就從早上8點多一直談到下午5點多。
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將考試看得很重要,但是,學生需要知道的知識遠比這些習題多得多,就像平面幾何所提供的不單是漂亮而重要的幾何定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在中學期間唯一的邏輯訓練,這是每一個年輕人所必需的知識。
從失敗中找到成功的路子
博士畢業時,丘成桐收到了來自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等6所名校的聘書,其中哈佛大學的薪水和待遇最高。然而丘成桐的導師陳省身教授卻建議他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所有出色的數學家都應當去一次,那才算對得起自己的數學人生”,即便那里的薪水比哈佛大學少了一半。
最終丘成桐選擇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因為他想讓他的事業走出一條有意義的路來。也正是這個純粹的決定讓他大為受益:“基本上全世界有名的學者都會去那里訪問,我能夠遇到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學者,而且比其他地方都多得多。跟他們交流,對我后來影響很大。”
自首次回國起,丘成桐便致力于中國數學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并堅信“中國要成為科技強國,必先成為數學強國”,為此他全職回國任教,積極投身于教育事業;通過“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丘成桐大學生數學競賽”等激勵青少年,并在家鄉梅州設立“丘成桐獎教獎學基金”,資助貧困學子,堅守對教育公平的追求。
學習如何從失敗中站起來也非常重要,一時的失意不應該影響一生的成就。如果總能在錯誤中找到繼續前進的方向,便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1976年,丘成桐證明了卡拉比猜想,使他一舉成為國際數學界的頂尖人物,也讓他成為菲爾茲獎首位華人得主,然而這一猜想的證明過程卻幾經波折。
最初接觸卡拉比猜想時,丘成桐認為這一猜想是錯誤的。1973年,剛到斯坦福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的丘成桐,在出席國際幾何會議期間提出了反證卡拉比猜想的辦法,以證明其錯誤性。
然而就在三個月后,卡拉比教授的來信讓他意識到了推理中的缺陷。經歷了兩個星期的失眠和反思,丘成桐意識到了卡拉比猜想的正確性,并最終在三年的推理中成功證明了這一猜想。
一門研究常常如此,在苦學和思考之后,可能發覺以前所走的方向完全錯誤,或是所要研究的問題他人已經完成。但從失敗的經驗中找到成功的路子,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門。(作者單位:中信出版集團)
- 2024-11-26《救命》——重生之我在清代當醫生(健康書櫥)
- 2024-11-06王一梅《茶鄉少年》:從生態童年到文化故鄉
- 2024-07-26讓古籍“活”起來——尋訪文溯閣《四庫全書》數字化影印出版工程
- 2024-05-20當短視頻遇上讀書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