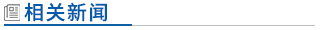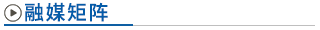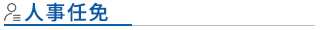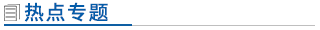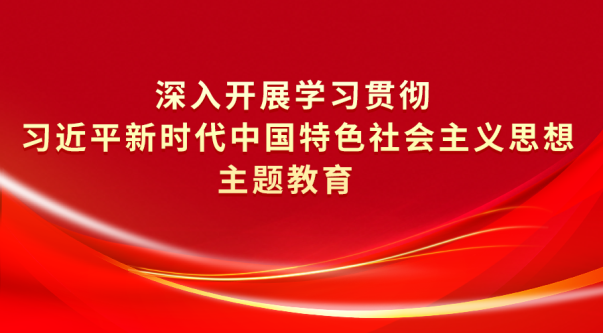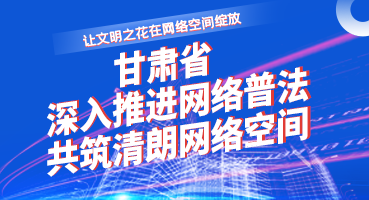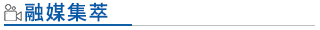6月5日下午,“新人文寫作與文化尋根——《補天:雍州正傳》”品讀會在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召開。北京大學陳曉明、漆永祥教授,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李洱教授,青年批評家叢治辰、樊迎春以及中文系王思遠、張聞欣、林孜等博士生、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張高峰,和本書作者徐兆壽,作家、該書責編、廣東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主任汪泉進行研討。
活動由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當代文學:區(qū)域與傳統(tǒng)”工作坊共同舉辦,青年批評家叢治辰主持會議。

《補天:雍州正傳》是知名學者、作家徐兆壽為家鄉(xiāng)涼州書寫的歷史文化傳記。徐兆壽以文學的筆觸,以文化大散文的方式,生動地再現(xiàn)了西北人的古今生活,是集歷史、哲學、文學、宗教、社會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為一體的一部關于大西北的百科全書,并融入了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一部有情有義的傳記。
該書分為三大部分,上部《天之道》回答了中國人關于天的問題。比如伏羲的“一畫開天”從科學的角度講開的是什么天,徐兆壽認為是時間和空間。那時候沒有文字,人們就用天空中的星星作為指引,但星星沒有形象和名字,于是人們便從大地或身邊的動物、山川入手對天空進行命名,為宏觀世界確立了時間和空間,這可以說是最早的科學世界觀。這是用今天的現(xiàn)代天文學可以證明的,所以這本書幾乎可以說是一部天文學著作。
中部是《地之道》,也就是尋找伏羲在距今一萬年和七千年之間是如何確立天道和地道的,是如何為天地間的生靈命名的,亦既天、地、人之間的關聯(lián)是什么。這就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元典《易經(jīng)》。這一章就涉及到中國文化的來源,即昆侖山的確切方位,黃河的源頭和神話誕生的地方。作者都用歷史文本和今天的科學知識進行一一對應,來確立其年代、方位。最為重要的是,要找到大禹的九州,然后把重點放在最有爭議性的雍州,為雍州立傳。
下部是《圣人之道》,是對伏羲、女媧、黃帝、堯、舜、禹這些上古圣人進行文學式的立傳,對他們所做的事情進行一次科學考古式的回答。本書借今天人類所有的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重新去偽存精,把上古時代留下來的一系列元典上的灰塵撣去,使這個天道明亮起來。也就是說,在這本書里,作者試圖使古今溝通,中外融合,這就叫補天。一是重新補中國上古時代確立的天道,二是用今天的知識重新證明并確立天道。
陳曉明教授說,徐兆壽是站在今人的問題上來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他認為天有缺,所以要《補天》。陳曉明教授講述:“我在讀兆壽過去的作品時,看到徐兆壽曾經(jīng)狂熱地閱讀西方哲學和文學,甚至科學。他在書里經(jīng)常談到尼采、海德格爾、福軻、德里達等,他還不停地談論老子、莊子、《論語》《易經(jīng)》《史記》《漢書》《后漢書》,還有《黃帝內(nèi)經(jīng)》等,但又不是掉書袋子式的,都是融化后的感想,有種古今、中外打通的感覺,至少他有這種通的理想。最為可貴的是,由于他是一位作家,所以他幾乎大多數(shù)的篇章開始都是從日常生活出發(fā),從我們熟悉而又有不同理解的現(xiàn)代材料出發(fā),帶入感很強,使本書顯得深入淺出。”
出身于甘肅,后在北大教書的漆永祥教授說:“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時期設四郡、通西路,西路通中國就通,中國對外的渠道也是通的,西路塞,國內(nèi)也不得安寧,這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個經(jīng)驗。兆壽出身于河西走廊,我出身于定西漳縣,我們都帶著對故鄉(xiāng)西北的思考而行走天下。在閱讀兆壽的著作時能感受到他的孤獨以及那種很高的追求。他思考西北,就是思考中國,也是思考世界。”
“兆壽表現(xiàn)的這種情懷,這種歷史感和現(xiàn)實感的交織,同時具備了歷史關懷和現(xiàn)實關懷,自己是很佩服的。”李洱說,“我看過他的《荒原問道》,后來又看他的《鳩摩羅什》和《西行悟道》,發(fā)現(xiàn)他談的問題都是大問題、大視野、大敘事、大觀念。在看到子思出現(xiàn)的時候,才意識到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它通過作者跟弟子之間對話,對中國文化一些源頭性問題、根本性問題做了重新發(fā)言,而且是對學生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發(fā)現(xiàn)的一些疑難問題從整體上做出回答,我覺得這需要非常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文化隨筆,是錢穆式的,同時又是易中天式的,融合了各種各樣的不同專業(yè)背景的知識、思想,試圖做出一種自己的解釋。”
叢治辰說:“我覺得兆壽老師是一個專門寫奇書的人,《非常日記》《荒原問道》《鳩摩羅什》都有些奇,《補天:雍州正傳》更是一部奇書,是一部非常規(guī)的書。這本書里面談到了天文學、地理學、冰川學,談到了《山海經(jīng)》《易經(jīng)》,有很多玄妙甚至神秘的東西,在別人看來可能有些深奧,而我則非常有興趣。這種跨學科的東西,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有人這樣寫作了。另一個感受是它跟《論語》有相似之處。我讀《論語》,最讓我感動的是那種場景感,很生動、很真實。《補天》和《論語》最讓我感動的地方就是行走,它們是生活化的,不是在課堂上教書,而是一塊生活,一起行走。學生遇到問題隨時問老師,老師也有回答不上的,然后繼續(xù)思考和回答。”
樊迎春說,在我看來,西部在這幾部書中已經(jīng)被徐兆壽老師對象化了,它已經(jīng)開始成為一個被凝視的對象,需要凝視之后再重新闡釋它,作為一個東部人,我對西部的所有想象都來自徐老師的闡釋,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鳩摩羅什》在我看來一是本小說,帶有一定程度的文學的虛構(gòu)和結(jié)構(gòu)在里面。從《西行悟道》開始走入非虛構(gòu)的講述,他開始提出和找到一些溯源的方法,《補天:雍州正傳》是又一次比較自信和大膽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說《西行悟道》還是在問一個終級的困惑:中國文化到底在今天還能不能給中國人以未來?還能不能說服世界并造福人類?從《補天》開始的那種焦慮和困惑以及懷疑和緊張都得到了本質(zhì)性的疏解,徐老師開始以《論語》和柏拉圖對話錄的形式,直接闡釋一個真理性的存在,這種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博士生張高峰、王思遠、張聞欣、林孜等都談了自己對本書的感受。張高峰說,徐老師是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入手進入創(chuàng)作和學術的,這個路徑在過去看是清楚的,但從《鳩摩羅什》和《西行悟道》開始發(fā)生轉(zhuǎn)向,他開始從西部、中國文化、哲學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學術方向,可以說是跨越重重的學科屏幛,試圖實現(xiàn)古今溝通、融通中外。我有幸在前年去過蘭州,從蘭州出發(fā),穿行祁連山隧道到達武威,實地感受當?shù)氐淖匀蝗宋牡臍庀螅莻€地方是廣袤的大地,有無垠的生命在生長。像徐老師這本書的《天之道》《地之道》,都是面向自然向度的悟道,進入到這樣的生命空間,當我們面對這樣的自然氣象,我們思考的肯定是和天地和生命有關的種種終極性的、本質(zhì)性的、生命本源性的思考。這些思考也會自然而然從我們血液里面涌騰起來。
王思遠談到本書時說,《補天:雍州正傳》中表現(xiàn)出的那種情感、情緒和孤獨,讓他覺得他和甘肅這個地方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他前不久有幸去了甘肅,實地感受了這個地方獨特的自然風光,它的自然非常復雜,除了海洋之外幾乎所有的地形地貌,它都存在。但在這樣一個擴大的、復雜的地形集合體當中,它又有歷史的癥結(jié),尤其當他們?nèi)鲋莸臅r候,這個地方既有文化的扭結(jié),也有戰(zhàn)爭的扭結(jié),同時這里也是某種歷史開始、某種歷史結(jié)束的地方,所以自然的風光和歷史的風景共同扭結(jié)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心境。
張聞欣說,之前拜讀了徐老師的作品,像《非常日記》,里面已經(jīng)提出關于信仰的問題。到后來的《荒原問道》或者《鳩摩羅什》時,開始把這個問題的答案牽引到宗教和中國文化。到了最新的《補天:雍州正傳》,徐老師更愿意把這個答案牽引到天道、地道和人道,天道是首要的存在,回到了中華文化自身的圈層里面去尋找這樣的答案。徐老師在數(shù)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對這樣一個宏大且核心的問題,鍥而不舍的探尋著。作品中有一種強烈的問道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并不是通過敘事,而是通過不斷的思辨、碰撞、問答,來尋找一種終極答案。
林孜說,我想把徐老師這本書定位為一種對話錄式的思想札記。為什么我要強調(diào)對話錄?因為我認為您這個對話錄恰恰反映了西方啟蒙主義的姿態(tài),西方啟蒙主義有一個高位和一個下位,但是您和您學生的對話,是一種互相平等的對話,我覺得這恰恰契合您強調(diào)的《易經(jīng)》當中沒有過分陽剛的一方,學生也不是過分陰柔的,大家是平等的。
本書責編、廣東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主任汪泉說,本來我們相約寫的是《涼州傳》,結(jié)果兆壽兄交寫的是《雍州正傳》,是整個大西北的前傳,也是涼州的前傳,我覺得這也是奇緣。在我看來,這本書是真正體現(xiàn)中國文化自信的一本書,是解開華夏文明源頭的一把鑰匙。本書《論語》式的結(jié)構(gòu)是一個奇跡,至今還沒有現(xiàn)代作家是這樣寫作的,這也是這本書一個極大的特點。
最后,徐兆壽表達了致謝。徐兆壽說,他的《荒原問道》《鳩摩羅什》都在北大開過研討會,今天又是《補天:雍州正傳》,這是北大對他的賞賜,他要銘記。他說,這本書可追溯到2005年,那時就已經(jīng)在打腹稿了,但在一次次修改,直到疫情三年,他在家里研究了天文學、地理學、冰川學等知識后,對《易經(jīng)》有了實體性的認識后,理解了上古華夏先祖的世界觀、方法論、倫理觀,于是便有了這本書。一定意義上講,這本書是偶然的、天賜的。他還說,這本書之后,將寫《開天》一書,這將是對《補天:雍州正傳》的進一步解讀。
- 2023-06-05【隴上學術鐵軍·第1期】張德芳:“簡”閱人生 “牘”有滋味
- 2023-05-31微紀錄片《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日常生活的獨白
- 2023-04-11戲曲傳承路上的“追夢人”——記第六屆“感動平?jīng)觥闭\實守信道德模范蒲虎勤
- 2023-03-21人物傳記《裴正學的醫(yī)路人生》捐贈儀式在武山縣舉行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