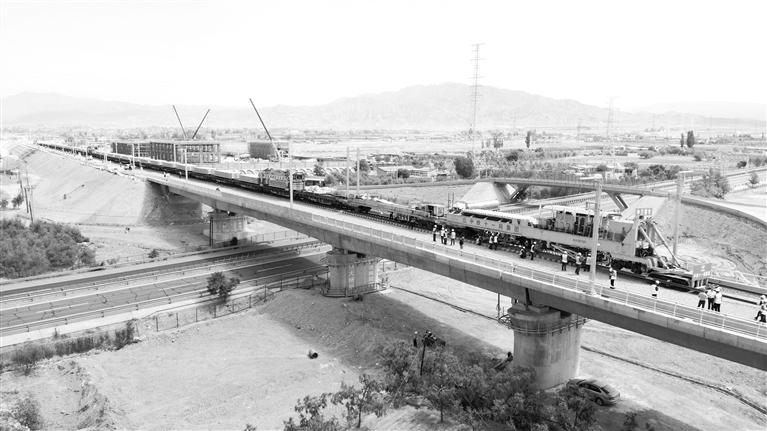在高原現場觸摸人間變遷 ——讀徐劍報告文學《金青稞:西藏精準扶貧紀實》
具有特殊地域情懷的作家大都是有氣象的,正若王蒙與新疆的血脈相連使其創作進入開闊深邃的境界,徐劍對西藏的一往情深也使他在作品中開辟出一片令人稱羨的精神高地。他曾20次入藏,出版7部有關西藏的作品,去年于疫情中再次進藏,寫出《金青稞:西藏精準扶貧紀實》(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12月出版),帶來新的邊地體驗。
徐劍對西藏最后一批退出貧困縣地區的關注不僅限于具體的事實和背景,他意識到一個雪山環繞的蓮花圣地的發現,藏族人民千百年來夢想世界的臨近,使他19個縣的采訪之途同時成為香巴拉和弄哇慶的追尋之旅。這位被稱為“老西藏”的軍旅作家熟悉這片信仰的土地,了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關于幸福和新生的真實感受。《金青稞》題記為松贊干布留下的遺訓,他希望普天之下老有所養,幼有所托,弱有所扶,“安得廣廈千萬間”。而他的期許今日正在新時代精準脫貧工程的收官階段基本變為現實。這是一部作家自己也期待已久的作品,感情上的醞釀遠在多年以前,所思所想更超越尋常采訪者的理念。
與有些近乎新聞體的報告文學作品不同,此書里引用的數字與匯報材料較少,場面描寫很多,內容皆為作者萬里之途中目擊與親身體驗的表達,又有由親歷產生的親切敘事,富有親和力。作者具體書寫了藏族同胞成批從高海拔地帶搬遷下來的情形,幾乎完全由國家提供的新型住宅區,新居的環境、建筑、設施,政府主動投資為貧困戶開辟經營產業,干部們為每一位勞動者設法安排就業崗位,以及建檔立卡戶們轉變觀念自強自立走上陽光大道的景象等。作者依靠采訪到的許多生動的事跡去觸動人、感染人,使人領略到西藏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金青稞》講述著扶貧故事,卻始終不局限于扶貧敘事,這是徐劍高于一些作者之處。脫貧是貧困人口人生中發生的重大轉折,卻還不是全部人生,他們還有著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并且,文學是人學,唯有寫活人物,才能激活讀者的閱讀。徐劍是深諳此道的。他筆下的每個重要人物,幾乎都呈現出完整的命運軌跡,這也是他從采訪起便力求做到的。人物不同,故事也不同。讀者很容易忘懷其他,深深沉浸在作者的講述之中,這是由于讀者喜歡把自己投射到人物身上,而作品中人物的不同個性和際遇也不斷啟發著他們對人生的認知。當然,他們也通過人物感知了時代。
徐劍眼中的現實,也是歷史、文化、傳統甚至哲學的投射。他走過三十九族部落,巡弋于上象雄、中象雄和下象雄舊址,還有城堡和藏北羌塘無人區,行至極邊之地,探尋西藏的人文歷史。抵達班公湖北岸,游走于中印、中尼邊境,探究古老的象雄文明、古格文明如何在一夜間消失。他并非意在廣泛涉獵,而是在“尋找歷史的注腳和文化密碼,以期從一個更高的歷史、文學和文明的視角,來思考詮釋這場堪稱人類奇跡的精準扶貧行動”。這就是作家與題材的關系,他養成的胸襟為當下扶貧題材創作帶來新的可能性。
令人感動的是,作者是在不顧個人安危和承受很大身體壓力的情況下實踐這次精神之旅的。5000米以上的海拔和不斷遭遇的生命禁區已使他難堪重負,開口說話需要很大意志力的支撐,又必須持續長時間的采訪。后期,莫名的咳嗽聲不斷,抗菌素無效,也使他的隨行者們擔心不已。但他堅持下來了,就像當初一定要來西藏一樣,心中動力來自他對這片神奇土地的摯愛,也來自他對信仰世界的尋找。
作者對報告文學藝術品位的追求是執著的,不斷在探索中。《金青稞》最先出現的人物是“他”:“成都飛往西藏邦達機場的航班一直沒有信息。他一次次仰望天穹,窗外,仍不見航班起降。”此后,這個“他”貫穿全篇,始終不知姓名。當然,“他”就是徐劍。而這個“他”產生了特殊的修辭效果,顯得陌生又平易,灑脫又凝重。由于“他”的引領,讀者輕易隨之起飛降落、深入藏地、走進村莊、待人接物、歡談笑語、頷首深思、浮想聯翩,終感全篇一氣呵成。其中功力在焉。
讀《金青稞》有一點讀小說的味道。作品雖然是在“報告”,講求精煉與清晰,但總體上氛圍是溫馨浸入的。作者不愿使讀者一目十行地了解大意,更愿讀者能隨他一起來到北緯二三十度現場,感受到雪域的嚴寒、天空的晴朗、居民的淳樸、神采的飛揚。他常運用色彩鮮明、形象細膩的語言狀物敘事,烘托起情緒的感染,使讀者不覺沉浸其中。自然,作者也一點不放棄發揮報告文學的優長,作品中不時出現思緒的縈繞、旁征博引的表達,又常使讀者豁然開朗。特別是作者善于在章節結束時畫龍點睛地點染一兩筆,其中情思交加,給人留下浮想。作者是在對創新報告文學文體進行新的嘗試。毋庸置疑,其功力在焉。
徐劍畢竟是徐劍。作者:胡 平(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
相關新聞
- 2021-04-29體現歷史和理論統一的“真”與“善”
- 2021-04-29略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讀本》
- 2021-04-29《白色莊窠》:鄉土變遷與精神鄉愁的抒情表達
- 2021-04-29雷鋒生命歷程的社會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