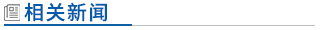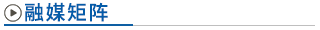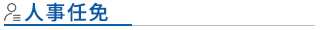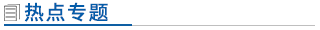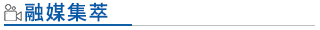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源遠流長的黃河水,從巴顏喀拉山脈一路走來,翻山越嶺,浩浩蕩蕩,流入一望無垠的渤海。
每當站在黃河岸邊,望著奔騰不息的河水,“逝者如斯夫”!我想,此生我和黃河的緣分是血脈相連、不可分割了。我出生在潁水之畔,母親告訴我那是黃河支流的支流,沿著河水一直走,就可以走到黃河。年幼的心中便生出無限的向往,我一定要溯流而上,親眼看一看我們祖國的母親河——黃河。在潁水河畔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和少年時光,我來到北大求學、工作,又響應國家教育扶貧和西部大開發戰略號召,帶領同學們來到了青海,為高原學子講述知識、教育和科技的魅力。走進72萬平方公里的青海,我到了巴顏喀拉山脈和星宿海的三江之源,那是黃河、長江和瀾滄江的源頭。
心有所念,一往無前。從三江源一路順流而下,我走到貴德,那里有形成于一億兩千萬年前的紅色丹霞地貌,壯美震撼人心的阿什貢峽。更有“天下黃河貴德清”的美景,我親眼目睹了如寶石一般在陽光下閃耀光澤的藍綠色的黃河水!那是黃河從雪山走來,未經黃土高原風沙洗禮的模樣。我也曾奔赴敦煌,在漫天風沙中到莫高窟朝圣和看望“敦煌女兒”——北大考古學前輩樊錦詩先生,每次望著她花白的頭發,仿佛看見半個世紀的時光一縷一縷穿過青絲,為她染上風霜的飽滿色彩。在大家看來,她是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是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在我心中,敦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她是我心靈的圖騰和歸依。每當站在鳴沙山上,望著月牙泉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景色,多少汗水和淚水都煙消云散,一切歸于心靈的平靜和充實。
每次到敦煌,都要在蘭州轉機,因為北京直飛敦煌的航班只有在旅游旺季才會開通。寒冬臘月里,坐在蘭州中川機場空蕩蕩的大廳,刺骨的寒意伴著呼嘯的風聲,我盼著黎明的第一縷曙光降臨,便匆匆奔向黃河鐵橋之畔的蘭州拉面館,一大碗熱騰騰的牛肉面湯,足以撫慰和溫暖身心。黃河水流到了蘭州,基本上還是清澈的,水中的沙石依稀可見,有不少老鄉手疾眼快,撿到形狀各異的水沖石,天然的紋路令人愛不釋手。寬闊的水面上,隨波起伏的羊皮筏子是每次到了蘭州黃河的保留項目。坐在輕便的羊皮筏子上,仿佛整個人都和黃河融為一體,隨著波濤起伏自由徜徉。
每逢不需要值班的春節假期,我會陪著家人回到黃河入海口東營,看著波浪接天的黃河奔流入海,享受闔家團聚的天倫之樂。如今,因為工作原因,我來到黃土大塬,世界上黃土層最深厚的地方,這里是周朝祖先播下中華大地農耕文明的起點,也是岐伯和黃帝論道的地方——中醫藥文化的發源地,更是陜甘寧邊區革命圣地:當年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走上抗日前線的起點。來到這里,看著亮黃濃厚的黃河水支流——馬蓮河、蒲河和茹河,從腳下流淌。想起小時候學會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黃土高坡》,“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真不曾想到,時光如水,歲月如歌。我自幼長大的潁水之畔,那是淮河的支流。淮河和黃河之間,有一條從東周就開始修建的人工運河“鴻溝”相連。跨越鴻溝,從淮河到黃河,又從黃河的發源地三江源到入海口東營,如今又來到黃河中游。
我想,蒲河和茹河交匯處的覆鐘山下的千年北石窟寺一定懂我此時此刻的心境。始建于北魏的北石窟寺,保存有全國最大的七佛殿。作為隴東石窟群的一顆璀璨明珠,如今由敦煌研究院代管。如意甘肅,一頭是敦煌,一頭是慶陽,雖然是在“如意”的兩頭,但是夜深人靜的時候,聆聽水流的聲音,仿佛在水中遙遙望見敦煌九層塔的風鈴,聽見樊先生輕柔的鼓勵和安慰。
千里黃河水滔滔。她一路走來,從三江之源到祖國東海,流經區域近75萬平方公里,滋養哺育了這廣闊天地中的人民和萬物生靈。千百年來,從《詩經》到漢樂府,從唐詩到宋詞,到處都有對她的贊美。母親河,這是我們對黃河最親切的呼喚。如今,站在這黃土大塬上,看著波濤滾滾的黃河水,唯有腳踏實地、胸懷江河,唯有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唯愿她一路奔騰、永不停息,見證我們中華民族的新時代!
(作者系北京大學黨委統戰部副部長)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